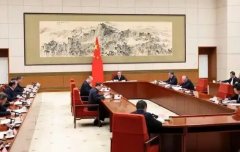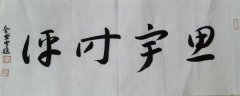【内容提要】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实力占比存在60%和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跨越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关键词】美国 对华竞争 “关键门槛” “战略阻断” 战略选择 【作者介绍】李义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国际战略、国际关系理论、台湾问题 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后,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致使中美关系深度恶化。在一定意义上,这是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对崛起国所施加的“战略阻断”行为。[1]所谓“战略阻断”是霸权国与崛起国战略互动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如果怀有独霸心态的霸权国从战略目标上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通常会在崛起国对自己的实力占比达到“忍耐极限”时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所谓“忍耐极限”一般是在崛起国对霸权国实力占比的60%到80%之间,此即顶层大国关系演变的两个“关键门槛”。[2] 现在,如何阻止中美关系进一步发生“螺旋式下沉”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关注。科学分析实力占比“关键门槛”对中美战略互动产生的影响,包括美国对华实施“战略阻断”的动因、方法及其困境,可以揭示某种规律。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施加的“战略阻断”行为,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一、美国对华施加两轮“战略阻断”行为 权势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将霸权国与崛起国间实力占比变化视为国际权势转移的主要根据。其关于实力占比最强指标性变化影响大国战略互动结果(战与和)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国际关系演变的临界问题,内里蕴含着“关键门槛”的逻辑。[3]此时双方对位关系突兀,权势转移进入剧烈变化过程,用奥根斯基(A.F.K.Organsky)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话说,如果一个大国的实力增长到至少为霸权国的80%,二者就会进入持平阶段;而这是权力再分配的基本临界,崛起国会被看作霸权国及其国际体系的“挑战者”。[4]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关于“战略临界点”的研究强调崛起国对霸权国实力占比60%的重要性,还有学者着重论述了40%到80%的阶段划分及其多重临界变化的重要性。[5]因此,可以认为顶层大国实力占比演变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由此构成的分析框架和解释系统可以对其间顶层大国战略互动过程进行更细化的解释,捕捉到它们在不同阶段发生的对应性关系,并做出必要的动态分析。具体来讲,60%是顶层大国权力持平(power parity)的起点,意味着崛起国作为全球性权力崛起,与霸权国构成权力持平的结构性态势;[6]80%是权力持平的“质变门槛”,表明崛起国有最终超越霸权国的可能。由于60%-80%区间对位关系十分突兀,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略互动趋于敏感,复杂的关系调整将影响终极结果。历史上,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关系调整一般有两种情形: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全面遏制打压,崛起国对霸权国发起挑战。其中,如果哪一方诉诸极端就会造成冲突或战争,战争可能是霸权国为遏制对手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也可能是崛起国为谋取上位而发起的进攻性战争。特别是,霸权国均可能在这两个“关键门槛”做出强烈反应,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 二战后的事实表明,在美国与崛起国之间并没有出现“关键门槛诱发大国战争”的现象,除美苏争霸外也不存在崛起国主动挑战霸权国的情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确实多次首先动手打压崛起国,而且一般选择在60%“关键门槛”前后;其时,美国对崛起国的崛起产生战略焦虑,多方面下手对崛起国进行扼杀。同时,由于对大国战争前景无法预期带来的恐惧,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通盘算计,美国更多是在战争与和平选项之外对崛起国采取“战略阻断”行为。较为明显的是,此时崛起国将强未强,跟美国实力悬殊,美国对其实施“战略阻断”占有明显优势,出手取胜把握较大。不过,如果崛起国奉行谨慎而又有谋智的战略,保持战略定力并平稳跨过60%门槛,营造出60%到80%+阶段的有利态势,就能够防止“战略阻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推动权力持平的演进态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战略阻断”行为有历史先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正是一个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并屡获成功的老手,它便是选择60%门槛前后动手,将崛起中的三个“老二”日本、苏联和欧盟都整下去了。 1984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债权国,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1988年日本GDP贴近美国60%、以后还超过60%,但“广场协议”效应发酵,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陷入“失去的30年”。日本峰巅时期的GDP是5万亿美元,如今却低于此数,不及美国五分之一。苏联工业产值在1978年达到美国60%,经济总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曾达到美国60%,但美国抓住其软肋,依仗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发起以“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的军备竞赛,做空并拖垮苏联经济,埋下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美国对欧盟的整肃也与其GDP超过自己60%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欧元诞生让它动了杀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盟宣布欧元为欧洲单一货币并实行统一货币政策,这让美国判定欧盟将是“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全球性挑战”。美国并没有重复使用“广场协议”那样的高压手段,而是以北约名义发动科索沃战争,导致欧洲地缘环境迅速恶化,外资掀起撤资潮,欧元地位骤然跌落。以后受伊拉克战争、2014年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及难民潮等影响,欧洲投资环境不断恶化,欧元受到多重打击。在2022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中,直接受害者是乌克兰,但“次生灾害”影响最大的是欧洲。 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美国曾经接连整下去日本、苏联及欧盟,说明美国对特定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取得过成功,并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战略阻断”行为旨在维护霸主地位,起因于美国的霸权意志而非其他,因此不管谁,只要是被其视为威胁的崛起国都要扼杀下去,即使如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高度同质的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第二,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和日本的“战略阻断”,即在政治上遏制苏联,在经济打压日本,几乎同时进行。这说明它不仅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有相当的实力,还有特殊的谋略和技巧。第三,美国对二战后的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尚未诉诸过战争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打压、政治孤立、地缘冲突及代理人战争等多种手段阻止它们兴起,根除对自己的挑战与威胁,但使用更多的是软硬兼施、量身定制的特殊手段。第四,60%前后是美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阻断”的“关键门槛”,后者都跌倒在60%门槛前后,美国施加“战略阻断”逐次成功,仍居于权力分配和国际秩序的顶端,其他大国无法跟它真正达到权力持平。 美国对华已经采取两轮“战略阻断”行动。近年来,美国政治人物不断喊出“美国第一”口号,旨在确保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不容忍出现同等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60%门槛便仍然是其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基本临界,不过这次遇到了一个更特殊的崛起国中国。在以接触战略演变中国、使之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未获成功后,美国直接诉诸“战略阻断”行为。从时间上讲,美国对中国有意识的全面遏制打压自2014年后起手,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全面铺开,接连实施了两轮影响深远和手段狠辣的“战略阻断”。由此,中美战略互动进入异常复杂而敏感的阶段。 首先,美国重塑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关键门槛意识”深刻影响政策制定。从根本意义上讲,战略定位决定战略竞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就是决定是否进行“战略阻断”以及进行什么样的“战略阻断”。特朗普上台后不久,美国政府重塑对华战略定位,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这种带有颠覆性含义的用语在美式文件中十分罕见,特别是“修正主义国家”的战略定位实际上比“战略竞争对手”在性质和量词上更严重,因为该用语是升高到挑战和破坏国际秩序的高度,认定“竞争对手”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者和倾覆者,必须从现在的位置上除掉;换言之,如果把你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就会往死里整你。由于特朗普政府完成对中国新的战略定位,经过推出三个战略报告和一个战略文件的充足过程[7],其结论被认为是美国两党、府会、战略界和社会多数的“共识”,在偏保守的美国社会这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拜登上台后,其本人及政府要员的重要讲话多次谈到中国定位,拜登总统使用了“战略竞争对手”、“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等措辞,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中美是“对抗性与竞争性的关系”,中国是“本世纪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最终,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定位锁定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主要战略威胁”。2021年3月白宫公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将中国说成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的竞争者。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备实力实现该目标的竞争对手”,并将今后10年定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美国要用10年功夫解决所谓“中国问题”。[8]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完成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阻断”的时间表。总之,从“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双定位到“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尽管文字表述有所调整,但美国两届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特别是战略意图的本意并无实质性变化,而是有着非常强的延续性。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从根本性质上重塑对华战略定位,说明霸权国的“关键门槛意识”发酵,严重渗入对华战略认知并造成其极度扭曲,成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动因。 其次,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先后实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2018年3月,依照国内法而非WTO相关规则,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由此开启了来势汹汹且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战。很快,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制裁打压延伸到科技、金融等领域,在贸易战之外又强加对华科技战和金融战。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一步实行极限施压,内容包括经济脱钩、科技断链、政治敌视和文旅禁限等极端做法,甚至外溢到地缘政治领域诉诸对抗行动。由于美国对华贸易战骤然升级到极限施压,以全方位、全政府方式强力打压中国,在做法上大大超过当年打压日本的程度,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对此,中国不得不明确表示“一直是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一定奉陪到底”的立场和态度,并采取了有力的反制措施。 面对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拜登上台后号称要与之进行“高强度竞争”并务必取胜(又译“竞赢中国”,outcompeting China)。由此,美国方面继续推行对华强硬贸易政策,加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科技领域,强调高科技是保持美国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是中美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场所”,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及中国投资高科技领域,实行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最近拜登签署总统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与前任有所不同的是,拜登重视同盟关系和价值观因素在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将之作为实施对华“战略阻断”的重要手段,不仅加强对北约控制以主导大国竞争,而且在“印太”地区拼凑“小北约”,以塑造所谓“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与此同时,美国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加大干预和制裁力度,频打和大打“台湾牌”并有在台海地区制造代理人战争的企图。总之,在所谓“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下,实际上竞争更多带有对抗成分;区别于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四面出击的特点,拜登政府在重点领域更有选择性地打出套路深花样多的组合拳,尽管其近来以“去风险化”代替“脱钩”一词,但并不能掩盖已经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的严重事实。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明显是对华“战略阻断”行为的继续。 再次,2014年至今“修昔底德陷阱”叙事流行,美国政策复归现实主义逻辑,成为“关键门槛”敏感期内美国对华施加“战略阻断”的“心理和认知伴奏”。恰恰是2014年后,“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在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受到热议,2015年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走向战争吗?》(The Thucydides Trap: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一文,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书。伴随着“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讨论,美国政界和战略界均有人加码炒作“中国威胁”,甚至出现鼓吹中美必然冲突的论调。由于这种叙事的推波助澜,中美关系不仅“回不到过去”,而且“修昔底德陷阱”似的问题趋于严重。[9]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出现复归现实主义的倾向,突出地缘围堵、同盟强化和阵营站队等传统做法,美国对华政策暴露出明显的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迹象。应该说,美国政策领域的这些变化,与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施加的“战略阻断”行为高度一致,并且成为这两轮“战略阻断”攻势的显著标识。 二、美国对华实际施加“战略阻断”的根源 自21世纪初以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整体发生深刻演变;与此同时,顶层大国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对位关系十分突兀。其中,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使双方实力水平接近,导致顶层大国之间出现显著的权力持平,即中美权力持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战略互动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呈现出新的特点;而从根本上讲,美国对中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存在着大的时代变迁背景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原因。 大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发展阶段理论(the theory of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在解释起飞现象时说过,起飞是在短期内出现的高速增长和跃迁发展,一般是30年;[10]崛起的逻辑同样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40余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走完的路,21世纪前两个10年更是崛起的迅跑期:第一个10年经济总量接连超过意法英德日等经济列强,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10年经济总量跨过10万亿美元门槛,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大幅缩短。艾利森曾惊叹:“在过去20年中国开始在诸多领域崛起,崛起幅度和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还没有时间感到惊讶”。[11] 在这两个10年中,2010年、2014年和2021年是3个带有标志性的重要年份,与跨越或接近实力占比“关键门槛”密切相关。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跟历史先例明显有别的是,从此至今已有13年,中国的这一地位一直没有被撼动,也就是没有被其他强国反超过。现在分别居欧洲第二、第三的英法,分别居世界第三、第四的日德,彼此间GDP总量多次发生过反超轮替现象;巴西是40年间GDP第一个被中国超过的国家,但中巴之间数次出现反超情况,直到1996年中国再次超过巴西才使之“绝尘而去”。此后,中国赶超的对象转向欧日等经济列强,而2010年后赶超对象只剩美国。到2014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进入世界经济超强俱乐部(只有美中),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虽然中国并不接受PPP公式而仍以贸易汇率计算GDP,但由于另一项更有意义的指标即中国跨过60%门槛,中美权力持平已经到来。到2021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7.82万亿美元,对美实力占比跃升到77%,这意味着已经接近实力占比80%第二道门槛。 在以上两个10年和3个重要年份为标志的顶层大国关系演变中,中国崛起进程持续推进,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强劲势头。首先,中国并非仅仅超越某一个大国、而是接连超越西方主要大国,并且使顶层大国之间的权力持平提前到来,这说明中国崛起是一个持续性极强的过程。其次,中国连续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第一波超过意法英,第二波超过德日,第三波赶超美国,是一个不断超越却没有被反超的过程,说明中国崛起无法阻挡。2010年以后中国对日德的占优差距越拉越大,与美国的占比差距不断缩小。现在中国GDP是日本3倍多、德国4倍,这意味着它们再赶超上来很困难,权力持平将发生在中美之间。再次,由于2021年中国对美实力占比跨过3/4线(77%>75%),中美实力占比出现黄金交叉;中国在大国关系演变中占据主动,它跟几个主要大国之间发生了位置变动,而其他大国之间彼此位置没有太大变化。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经济崛起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确实也有很大提升。 与中国崛起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所谓相对衰落并非现状中已呈整体颓势的绝对衰落,而且指实力占比和影响力存在着走下坡路的趋势。相对衰落的“相对”表明时间和参照系两个因素的重要性。从时间来看,美国迄今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唯一拥有超20万亿美元GDP的国家,其现代化程度及科技、军事、金融等实力仍居世界首位;但长年来美国GDP相对优势持续萎缩,GDP世界占比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下降,如二战结束时GDP世界占比50%以上,自2007年后再也没有超过25%,最低时21%,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2013年到2021年平均为18.6%,远不及中国的38.6%。特别是,将本世纪头20年作为观察问题的时间尺度,就会看到中美实力占比的标志性变化,即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集中于这20年。 从参照系来看,如果将中美和其他大国都作比较,中美实力占比在接近,但美国相对其他强国的优势不仅没下降、反而在上升;而从多极化、区域化等整体性因素看情况则大为不同,区域联盟可以将其他强国的实力集中整合,如以欧盟、而不是法德实力计算,美欧差距并不大;中国GDP也是在2021年才超过欧盟,真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非西方势力崛起带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东升西降,经济区域主义的整合(如东亚、东盟、RCEP、金砖国家),都是对美国地位和实力的挑战和稀释,削弱了其全球经济影响力。而在政治层面,美国霸权控制和战略信誉不断走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呈收缩之势;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深刻调整,今非昔比。其实,美国是否真的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它自己。多年来,美国存在财政赤字、债务危机、社会撕裂、种族矛盾及政治极化等诸多问题,国内治理面临极大挑战,其长期独有的强大修复机制将在困境中再受检验。过去,美国依靠这种修复机制不止一次从衰退中走出,重振超级大国雄风,如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80年代里根。但正是上述符合美国国情的内因,使其曾经灵光的修复机制被不断销蚀,出现了明显的钝化趋势。 总之,跟自身巅峰时刻、中国迅速崛起及国际关系整体变化相比,美国相对衰落乃是一种现实,也是一个演进中的趋势;崛起国与之出现权力持平不可避免,并且这种势头将继续向前延展。从终极意义上讲,美国只有失去美元霸权、核心科技和军事实力等领先地位,进而在国际秩序中丧失霸权,才可以说到绝对衰落。在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作用下,经过两个“关键门槛”,权力持平的到来与强化必然加剧美国的相对衰落。 结构性原因是“关键门槛”60%-80%区间的中美权力持平。从理论意义上讲,“关键门槛”属于国际关系结构问题的范畴。如前所述,在崛起国对霸权国实力占比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之间,二者进入权力持平阶段,彼此战略互动也随之进入关键时期。60%门槛是权力持平的开始,2014年起中国跨过对美实力占比的60%门槛,2021年临近80%门槛,这是中美权力持平的“质变门槛”。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此阶段中国对美赶超时间不断缩短,占比数据迅速提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美国10%的增长需要十几年,从60%到70%用了6年,最近从70%到77%只用了1年;按照易纲先生所说今后经济增速维持在5%到6%,[12]中国将很快达到美国的80%+。这意味着,中美实力占比结构和国际关系结构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第二,2021年中国对美实力占比为77%,首次跨越3/4线,中美综合实力占比在趋势上出现了对中国更有利的变化,并且这一趋势的继续是显著的。国际战略分析机构普遍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中美实力占比结构和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比较有利。 然而,问题也来了。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关键门槛”结构性变动的影响,美国主动对中国发起两轮“战略阻断”行动,试图将中国崛起进程阻断在两个“关键门槛”之间。首先,作为触媒,2014年有三个事实带有很强的指标意义: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按PPP计算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特别是对美实力占比达到60%。这三者加起来表明中国崛起无法阻挡,美国由此产生战略焦虑并开始采取对应性行动。特朗普上台后喊出“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等口号,这些跟他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心态和焦躁情绪直接有关。需要指出,特朗普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2014年的数据是一种刺激性因素,他极其看重2014年的前两项指标,虽然作为政治素人他并不懂60%门槛有什么含义,[13]但其外交政策带有突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对中国进行“战略阻断”的意识最强,出手最狠。 其次,2021年是权力持平的“加速时刻”,中国对美实力占比达到77%,中美实力占比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坐二望一态势明显。面对这种结构性变化,特别是80%第二道“关键门槛”的逼近,拜登上台伊始即单方面宣称要跟中国进行“高强度竞争”,试图通过多方面对中国施加的遏制打压,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甚至不惜将中国排斥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之外,以削弱和压制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尽管中国政府向美方清晰表明反对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但美国一再声称“不寻求与中国冲突或对抗,但要准备好激烈竞争”。比较而言,特朗普对华战略定位将中俄并列为“修正主义大国”和“主要安全威胁”,是出于政治素人的朴素认知和某种直觉;拜登政府的两份主要战略文件(《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国家安全战略》)则共同将中国说成是“唯一的竞争对手”。[14]这充分说明,拜登政府对中国进行“战略阻断”的意识丝毫不弱于特朗普时期,其做法甚至更加聚焦重点和缜密规划,试图将中国阻挡在80%“关键门槛”之前,也不排除要把中国“推回”到更为落后的状态。无疑,“关键门槛”的结构性变化对拜登政府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显然是继续实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的主要原因和依据。 综上所述,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国崛起既是跟欧日大国实力占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更是在此基础上跟美国实现显著权力持平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几乎两相同步,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唯一能够跨过权力持平两道“关键门槛”的崛起国。这是国际关系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但在客观上也使中美关系产生了某种结构性矛盾。由于在主观上倾向于从负面理解“关键门槛”问题,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严重偏差,陷入了“美国优先不容老二”的历史误区。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14年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一些消极变化,特朗普上台后迅速全面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战略互动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即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均从性质上重塑对华战略定位,并于2018年和2021年发动了两轮颇具规模的对华“战略阻断”行为,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成为实施“战略阻断”的两种具体手段。这种跟两个“关键门槛”相对应的关系既非巧合现象,亦非艾利森所说的“数据隐喻”(digital metaphor),[15]而是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关键门槛”结构性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权力持平的结构性矛盾和受此影响美国惯用的“战略阻断”逻辑。面对“关键门槛”对自己霸权地位及其主导国际秩序的影响(美肯定认为是“威胁”),美国不容忍作为崛起国的中国超过它,甚至不容忍中国待在现在的位置。由于中国很难像苏联、日本那样被轻易整下去,美国开始重演历史,施加升级版的“战略阻断”行为。这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全面深度恶化的深层原因。 三、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的困境 对美国说来有点惊悚,它遇到了中国这个极为特殊的对手。由于中国崛起具有明显的不可逆转势头,中美权力持平将经历一个非同寻常的过程,也是美国很难驾驭的过程。在权力持平的继续演变中,美国对华施加的“战略阻断”客观上将会失灵,若一意孤行可能加剧自身的相对衰落。虽然霸权国和崛起国均需妥善面对“关键门槛”问题,但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霸权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会更多地受到结构性制约。 第一,权力持平集中发生于中美之间,但美国已经错过60%这个实施“战略阻断”最易得手的机会。虽然60%构成权力持平的第一道门槛,对位关系的敏感容易触动霸权国神经,但中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权力持平即将进入80%+阶段。80%是权力持平的第二道门槛,80%+阶段对位关系更加敏感,“战略阻断”行为甚至会强化。但历史经验表明,有60%门槛前后实施“战略阻断”获得成功的先例,还没有跨过3/4线后得手的例子;[16]60%阶段做不到的今后更难做到,近年来美国实施对华“战略阻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其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之间的失调,战略能力很难确保实现战略意图。由于在当今世界,中美“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打倒不了谁”,[17]美国再想将中国打压下去谈何容易,它要这样做必须动用全部力量和资源、至少大部分力量和资源;即便如此,美国不仅会面对“伤敌亦自损”的效果,而且将跌入“大国兴衰律”的陷阱,因为这从根本上违逆了国际关系演变的趋势规律,等于主动自陷霸权反噬怪圈。 第二,如果美国在使用其他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以战争方式进行“战略阻断”,那么将面临三种无法预料且难以控制的情形:1、霸权国把崛起国真的强压下去,但代价极为沉重,几乎相当于自残。历史上此类先例似乎常见,这也是权势转移理论所强调的“事实经验”。2、崛起国反手打败霸权国。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16个案例中不乏此例,[18]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兴衰律”亦将之撷为典型。[19]3、“黄雀效应”,即战争使顶层大国的实力和精力消耗殆尽,第三者在两强对抗中渔利,在两强崩溃后反而建立新的霸权。在某种意义上讲,80%及80%+阶段最容易发生美国极度忌惮的“黄雀效应”。美国学者吉尔平(Robert Gilpin)说过,霸权战争可能有助于巩固霸权国地位,“也可能引起未曾料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体系变革”。[20]美国对哪一种情形都无法完全控制,发动战争打压崛起国简直是赌上国运,可能给其霸权地位带来颠覆性后果。而对于中国来说,正如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两年前就指出的,超过60%(GDP总量占比)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阶段,如果中国保持适当增长(例如5%)并且战略选择恰当,最终将拥有比美国更大的潜在力量。[21]也就是说,在“关键门槛”的临界区间中国战略选择恰当,美国实施“战略阻断”的机会就越来越小,自己崛起成功的空间越来越大。 第三,中国奉行永不称霸政策,根除了权力持平过程极易发生的争霸现象,美国在道义上失去实施“战略阻断”的理由。历史上,权力持平阶段出现争霸现象几成定律,霸权国和崛起国在处理终极关系时往往通过争霸进行轮替,而这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冲突和战争。但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属性及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不会跟美国争霸,即使在实力占优时也是如此。毛泽东很早提出不称霸主张,邓小平明确宣布“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习近平强调“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22]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就是不做世界霸主,即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不谋求这种地位,而是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几十年来,中国公开宣示不称霸是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是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进宪法的唯一国家,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会在实践中重复国强必霸的逻辑,也使美国强行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缺乏道义正当性,在国际社会人心向背方面也站不住脚。 第四,在现实层面,与日本、苏联等比较,面对“战略阻断”时别人没扛得住的,中国都抗住了,美国对苏联、日本等分别施加的“战略阻断”手法对中国并不灵验,近年来针对中国综合使用对付前苏联和日本的策略,包括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围堵等都无法阻挡中国崛起。中美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关系;既很难在政治上打新冷战,也无法在经济上完全脱钩。最近,拜登政府一方面要跟中国进行“高强度竞争”,另一方面又说不会跟中国进行新冷战;一方面要“不惜经济代价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说搞脱钩不符合美国利益,就明显反映出美国在施加对华“战略阻断”时的矛盾困境。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之间,尽管美国强加的种种打压为历史罕见,但中国都顶住压力,崛起势头没有受到实质影响,综合国力仍保持上升势头;而美国接连实施的行动效果不彰,也并未扭转其相对衰落。总体上看,国际关系演变在继续按照自身逻辑、同时也是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演进;中美权力持平是一种惯性很强、突破常规的权力持平,美国很难按照自己意志逆转。由此,中美之间将保持较长时期的战略相持态势,中国无法挑战美国,美国也压不住中国、“惹翻了不好办”。 第五,越来越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整体制约成为“战略阻断”行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相当意义上,21世纪20多年来所发生的更多是国际关系的整体变化,这已然成为大国关系演变,特别是顶层大国战略互动的深刻背景。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交织叠加,中美权力持平虽使对位关系突兀,但其已深嵌国际关系的整体性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国际关系整体性至少发挥着三种制约作用:多极化制衡、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战略稳定。一是多极化制衡具有结构性功能,使“单极时刻”成为过去,霸权国难以为所欲为。权力持平在对位关系上促使权力集中的同时,需要面对国际关系整体的权力分散状态,冷战后多极化、区域化和去中心化已是国际社会“新常态”,压缩了权力集中诱发风险的空间。二是全球化下经济相互依存,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美及各国经济深植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经济脱钩和科技断链并非仅凭单方面愿望和行动就能做到。三是全球战略稳定建立在核威慑和国际规范的基础上,作为战后国际关系要件始终发挥着遏止大国战争和限制大国冲突的关键作用,是霸权国以战争方式进行“战略阻断”的主要障碍。总之,美国的“战略阻断”行为虽因对位关系敏感而带有惯性,但始终受到国际关系的整体制约和根本牵制;恰恰由于它跟国际关系演变趋势相逆,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相悖,因而实际上已经陷入无解的困境。 四、中国的关键战略选择 展望未来,中美权力持平以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为结构态势,以战略相持为互动态势,以80%“关键门槛”和80%+延伸区间为重要节点,以世界百年变局为时代背景。在此情形下,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以有效应对“关键门槛”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鉴于中美权力持平跟历史上的先例都不相同,具有双方对位关系与国际系统关系复杂交织的特点;鉴于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是美国施加的“战略阻断”行为,且这种行为仍然没有停歇;鉴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在80%+延伸区间将更为凸显,将是世界百年变局演进中的主要矛盾;因此,在中美较长时期的战略相持中,中国只有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并开展成功外交,才能降低和消除美国“战略阻断”行为的不利影响,保证自己能够成功崛起。 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在当前就是努力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是保证中国崛起的决定性条件,是防范和反制“战略阻断”行为的底气所在。应该说,在中美权力持平的趋势下,“目标纲要”的战略意义十分凸显,实现其规划目标是真正的谋时造势。一是中国将超越GDP而全面扩张国力内涵,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和现代化程度。GDP总量并不等同于全面国力,实力占比的衡量标准不仅要看GDP数量,更要看GDP结构和质量,质言之,今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关键是科技、军力和金融。当“纲要”的相关目标都实现了,防止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阻断”才有坚实保障。二是中国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跨越过3/4线,而80%+是最后解决权力持平终局的关键阶段。在历史先例中,3/4线是前苏联和日本都没能跨越的门槛;在现实案例中,跨过此线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更好前景。不过,需要重视和警觉的是,虽然中国总的崛起态势良好,但由于外部环境“风高浪急”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中国跨过3/4线仍存在着发生个别波动的可能,如2021年中国对美实力占比达到77%,2022年却又有所回落;[23]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有效保证中国自身发展的韧性和崛起的成效,提高对大国战略互动态势的塑造能力,进一步夯实中国在顶层大国权力持平中的地位。 其次,通过战略对话解决美国对华战略认知问题,搬除“战略阻断”这个“拦路虎”。美国重塑对华战略定位并实施“战略阻断”行为,固然有实力占比变动的结构性原因,但其对华战略认知陷入误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在中美关系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中国方面总是以元首会谈及通话、外长发表文章及会晤等多种形式,反复强调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问题。例如王毅主任曾经明确指出,中美关系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24]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和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对“关键门槛”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及对各自的影响,肯定有不同的理解和把握,这并非是不正常的。恰恰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双方确立并维持一定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机制。通过战略沟通和对话,可以使双方达成必要的战略互信,化解乃至消除彼此的误会和误解;可以削弱和控制“关键门槛”引起的结构性矛盾,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和事态进行有效管控;从根本上讲,是要通过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跳脱“霸权国-崛起国”的传统循环模式。近来,中国方面一再重申,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相向而行,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所要构建的是共存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更不是对抗关系。这些应该是理解“关键门槛”问题的一把钥匙,是彼此建立正确战略认知的核心要义。 第三,切实发挥成功外交的保障作用。确保实现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保证自己在中美权力持平进一步变化中占据有利地位,特别需要发挥外交的作用。国际关系常识告诉我们,外交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运用得当会延伸和扩张国家实力;当然,这里指的是成功的外交,而非失败的外交。首先,成功外交必须做到战略目标清晰,应该遵循国际关系规律,有力把握“关键门槛”问题的实质,充分利用和扩大80%及80%+阶段的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确保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根据权力持平的特殊性,有效驾驭中美对位关系和国际系统关系复杂交织的特性。成功外交不仅能使对位关系脱敏,而且能在国际系统关系中寻优,不断拓展战略机会和战略空间,实现权力持平中的最大利我。再次,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以成功外交扩张和延伸国家实力,而不是消耗自己的力量。在权力持平过程中,中国跟美国尚存较大差距,跟其他发达国家也在不同领域存在差距,达成合理的权力持平要付出更多努力,尤其需要成功外交去补强所存在的差距。也就是说,成功外交要始终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也要有新时代的担当作为。 【文章来源于《现代国际关系》杂志2023年第8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24年第1期全文转载;并被翻译成英文发表于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imonthly),Nov./Dec. 2023, No. 6.】 [1] 有学者把霸权国实施的“战略阻断”行为称为“杀老二”。见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参考消息》,2016年8月24日。 [2]本文在谈到60%、70%、80%等时,均是实力占比数据,指崛起国综合实力占霸权国的百分比,是“关键门槛”的数字化表达。 [3]A.F.K.Organsky,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8, Ch.14;A.F.K.Organsky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44. [4]A.F.K.Organsky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p.44. [5]王帆:《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第137-145页;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4页。 [6] “权力持平”是权势转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A.F.K.Organsky, World Politics, Ch.1 and Ch14. [7] 2017年12月和2018年前两个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密集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并于2020年5月公布《对华战略方针》文件。 [8]TheWhiteHouse,Th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9]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被认为是霸权国和崛起国、特别是“世界老大”和“世界老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权势转移理论范畴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10]参见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11]Graham Allison,The Geopolitical Olympics: Could China Win Gold?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geopolitical-olympics-could-china-win-gold-190761?page=0%2C1. [12]易纲:《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研究》2021年第9期,第1页。 [13] 从某种意义上讲,2010年是中美关系因“关键门槛”问题发生性质变化的前场预演。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实力占比刚好达到40%。恰好这一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出现大幅倒退。这说明,中日关系恶化也有结构性原因。由于中美权力持平阶段还未到来,所以中美关系还未发生明显恶化,但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加重,其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均出现调整迹象。2012年前后,奥巴马政府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并试图主导建立TPP,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遏制中国的企图明显。而正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由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对美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14] 2021年3月,白宫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将中国说成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的竞争者。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备实力实现该目标的竞争对手”。 [15] ALLISON Graham,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p.239. [16] 这里,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跟其他崛起国非常不同,中国制造业产值不仅早已超过美国,而且超过美日德等的总和;而其他崛起国如日本和前苏联的制造业产值均未超过美国的70%,欧盟未超过美国的80%。 [17]《王毅:中美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打倒不了谁》,新华社,2022年9月19日。 [18] ALLISON Graham,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244-286. [19]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xvi. [20] Robert T.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9. [21]John J.Mearsheimer,The Inevitable Rivalry: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21,No.6,pp.48-58. [2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0页。 [23]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3%,2023年预期目标是5%左右,但普遍认为“左右”是以5%为底线。2023年两会后,OECD首先调高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为5.3%;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调高了中国经济增长指标,分别为5.6%和5.2%;花旗银行则将中国经济2023年增长预期从此前的5.7%上调至6.1%。前不久,中国官方公布今年上半年GDP总值同比增长5.5%。 [24]《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新华社,2022年7月9日。 (编辑:思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