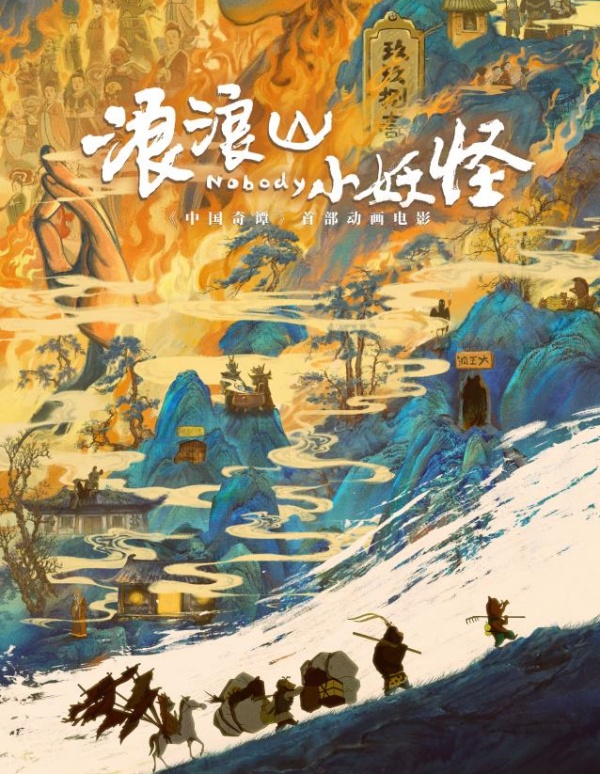|
政治对贝多芬获得崇高地位也有推动作用。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欧洲传统格局,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无序的状态让很多人转投音乐,将音乐视为避难所。在混乱的局面下,贝多芬显露出了最高的威望。而且,霍夫曼1810年对第五交响曲的评论显示出贝多芬名望的快速增加,这种名声飞速增长的状况符合了二十世纪初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定义的“政治浪漫主义”倾向——对消失的中世纪基督王国和神话国家怀抱的泛德式思愁。贝多芬虽然有着相信四海一家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但对这种愁绪也并非无动于衷。最近的一些研究,尤其是马修的《政治贝多芬》和斯蒂芬·拉姆夫(Stephen Rumph)2004年的著作《拿破仑后的贝多芬》(Beethoven AfterNapoleon),着重关注了贝多芬晚年的关系变动,探讨了甚至包括超凡脱俗的晚期四重奏在内的作品里的政治内涵。这类讨论也许会被斯瓦福特当作装腔作势,但它对贝多芬现象诞生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读。 拉姆夫和马修分别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在作品中都研究了常见曲目——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曲、“菲岱里奥”和“庄严弥撒”——同时也关注了很多贝多芬爱好者所忽视的宣传性作品。拿破仑于1809年占领维也纳时,爱国情感正在奥地利人民当中滋生。贝多芬早年虽然热衷法国,但当时也有了反对法国的倾向。1813年,他写下战争交响曲“惠灵顿的胜利”,来纪念惠灵顿在维多利亚击败拿破仑;一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华而不实的清唱剧“光荣时刻”,来歌颂维也纳会议和奥地利的复兴。早期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浪费了贝多芬的天赋,或把它们当作讽刺及模仿的习作。而拉姆夫和马修则认真对待了这些音乐,认为它们是贝多芬向晚期过渡的作品。拉姆夫指出,“惠灵顿的胜利”结尾处极快的二重赋格,预示了第九交响曲临近结尾处的对位的欢庆。贝多芬自己也对这些作品比较满意,他在批注一份否定这些作品的评论时写道:“我拉出来的东西,比你的任何思想都要强。” 长期以来,传记作家一直坚称,拿破仑时代的动乱和随后的王朝复辟让贝多芬遁入了一个隐秘的空想世界。他们还认为,听力的丧失让他远离了日常事务。相比之下,拉姆夫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形象,展示了一个信念趋于保守、越来越信奉“政治浪漫主义”里的民族审美性的作曲家心神不宁的状态。贝多芬晚期的印记——对已故大师的兴趣与日俱增,尤其喜爱巴赫与亨德尔;热衷于复调和对位;对自由奔放的、有时显得不够成熟的抒情民歌产生浓厚的爱好——体现出来的不是进步,而是紧缩倾向。在这些作品里,甚至在第九交响曲中,晚期的理想主义突然出现,表达方式变得有些保守,末乐章开头部分骄傲的男低音独唱——“哦朋友,不要用这样的声音!”——仿佛在宣称这是对权威的救赎之声。 马修在《政治贝多芬》里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观点,然而他的阐释所蕴含的意义具有惊人的广度。在他笔下,贝多芬从作曲生涯之初便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进行永恒的抗争:书里有些地方描绘了拿破仑时期维也纳的战时图景,号角声、进行曲和战争歌曲响遍大街小巷。贝多芬接纳了这些战争元素,把它们转化成了更纯粹的器乐语言。这种置换,在马修认为“以全部的号鼓、赞美诗与壮烈爆发营造出政治气氛”的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里体现得甚至更为明显,只是没有明确的政治指涉罢了。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里含有被某些重要使命所激发和唤醒的强烈能量。但这是什么重要使命?埃斯特班·布赫(Esteban Buch)1999年的著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一段政治史》(Beethoven’s Ninth:A Political History)记载了这部交响曲在不断循环的语境中的地位,从德国的沙文主义到马克思信徒的国际主义,再到以“欢乐颂”作为“盟歌”的欧盟的自由主义。 “晚期的音乐把听众变成了诠释家,”马修写道。历史和伟人的光环在我们耳边展开,冲向未来,让我们陷入疲于奔命的阐释中。这,或许就是贝多芬现象的核心。他拥有空前的自主性,哪怕面对资助自己的贵族,他也决不低头。他的大多数重要作品都冠以奏鸣曲、四重奏、协奏曲和交响曲之名,以抽象的、非描述性的形式传达思想。然而这种从奴性和功利中解脱出来的自由也有矛盾之处:这种音乐虽然摆脱了当下的束缚,却成了未来的俘虏。“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马修写道,属于“永远在寻找合适出场时机的天成之作。”由于它们压制了我们自己的梦想和热情,我们正面临将它们以空洞的方式消耗殆尽的危险。这种危险有可能让我们永远空虚。甚至已不只是一种危险了:圭列里的《前四个音符》的最后一章谈到,在E·T·A·霍夫曼笔下承载着敬畏与恐怖的工具,如今已成为毫无意义的迪斯科舞曲、嘻哈音乐、歌谣和手机铃声的片段了。 贝多芬能躲避这种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无意义的不朽吗?马修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他身上的偶然性和不合常理之处”:他的野心,他的机遇,他的背离,他审美的偏差,甚至他的失败。“惠灵顿的胜利”和“光荣时刻”等次要作品——“差的”贝多芬——显示出作曲家容易受到低潮期的影响。如果你认可贝多芬时代的流行作品——马修举的例子是伊格纳兹·莫谢莱斯(Ignaz Moscheles)的钢琴奏鸣曲“1814年奥地利首任皇帝弗朗茨陛下返都维也纳之反响”——你或许就能对当代音乐有更多的忍耐了。经典是个巨大的幻影,随着让人失望的过去的消逝而产生。 最近的出版物里,在还原贝多芬真实命运方面最下功夫的是一部虚构作品。桑福德·弗里德曼是一位纽约作家,2010年以八十一岁高龄辞世。他凭借一系列小说赢得读者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的成长小说《图腾柱》(Totempole)。《与贝多芬对话》并未在他生前出版;由于关于作曲家或其他类型音乐家的知识分子小说十分稀有,《纽约书评·经典》(N.Y.R.B. Classics)便付出一系列努力助其问世。这本关于贝多芬的小说描述的并非他如日中天的时期,而是他状似老怪物一般的风烛残年的生活。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