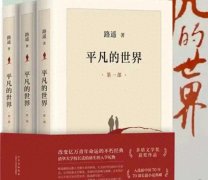胡乔木的诗情
陈 鹏 早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在一个重要场合对人说,找乔木,有饭吃。后来,小平同志曾这样评价胡乔木,他是我们“党内第一支笔”。
在掌管意识形态,指导重大文件起草、参加理论著述的间隙,胡乔木以诗词构筑着另一个精神世界——那里有泥土的芬芳、青春的火焰,也有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辨。他的诗情,恰似一株生于政治岩缝中的乔木,始终向着文学的苍穹伸展枝叶,吐出芳香。
笔底惊雷初绽时 胡乔木的诗情,启蒙于故乡盐城的书香门第。父亲胡启东擅五古七律,著有《鞍湖诗存》,家中诗教如春风化雨。在扬州中学求学时,他因一首五言古诗获“淮南才子”盛赞,其中“夏木变凝碧,秋虫鸣繁钟”一联被批“二句入古”,少年才情已露锋芒。 十八岁那年,他在校刊发表新诗《别辞》,以决绝之辞告别旧世界:“我要来奏一个粗暴的调子”——这不仅是青春宣言,更是他投身革命的序曲。
诗中想象战友“倒卧在血迹模糊里”,脸上却带着“战斗过来的红色欢笑”,炽热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理想在此交织。更难得的是,他对中西诗学兼收并蓄。在清华读书时,曾手抄译诗成册赠友,大胆点评名家:“郭沫若译诗雄浑,周作人清雅,而朱湘《秋曲》未得神髓!”其胆识与慧眼,已显大家气象。
从田园牧歌到战鼓雷鸣 1937年,乔木发表于《希望》杂志的《挑野菜》,是他早期新诗的代表作。全诗八节复沓“挑野菜哟”,以童谣般的节奏展开江南春日画卷: “瞧天!春来第一个好太阳,坐在地上你闻得见香。” 少女的娇嗔(“今晚上妈说要煮一锅”)、少年隐秘的情愫(“草花里虫儿飞进我的眼”)充满生活意趣。然而第七节笔锋陡转,借路人对话点出时代悲音:“回老家?唉,你的心肠真好!还不一样?我往哪里逃?” 田园诗瞬间跃动起抗战的脉搏。 此诗更是他探索新格律的里程碑。每行四音顿,轻重音如“扬抑抑扬”的鼓点;韵脚隔节呼应,如旋律回环。学者誉之为“真正的珍珠般的诗篇”,为汉语新诗开辟了一条融合民歌、古典与西方韵律的路径。
延安时期,乔木的诗笔化为战歌。冼星海为他谱曲的《青年颂》如号角震彻山河:“谁能比我们大无畏的勇敢?长江水从西天飞跑到东天!”而写给妻子谷羽的《人比月光更美丽》,则在烽火中绽放出的柔情: “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铁血与柔情的双重变奏,映照出革命者的心灵。
风云时代的词章志 1960年代,毛泽东诗词风行全国,胡乔木亦“试写旧体以应时风”。1964年国庆夜,他仰望长安街火树银花,挥就《水调歌头》: 万朵心花齐放,一片歌潮直上,化作彩星驰。“心花”与“歌潮”的意象交响,将政治庆典升华为星河灿烂的奇幻诗境。 次年重读《雷锋日记》,他连填四阕《念奴娇》,以古典词牌书写新时代英雄。其中“身是螺钉,心怀天下,有限成无限”一句,将政治标语点化为哲学箴言;而“一朵花开春不算,要看百花齐吐”则暗含对集体主义精神的礼赞。
特殊年代里,他的词作更显深意。《菩萨蛮》中“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偷火”,借普罗米修斯神话隐喻革命者的盗火精神;“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则以反差笔法暗写时局波澜。
笔墨间的灵魂相照 胡乔木的诗情世界中,与毛泽东、钱钟书的交往尤为动人。 1957年讨论《蝶恋花·答李淑一》时,胡乔木直言“忽报人间曾伏虎”的“曾”字不妥,毛泽东却拍板定案:“就是‘曾’了!” 二人“就诗论诗”的坦率,超越了政治身份的藩篱。而胡乔木在病中毛泽东建议“专看闲书,不管时事”,才使他暂卸重担,孕育出六十年代的词章华彩。
1982年胡乔木作七律《有所思》庆七十寿辰,钱钟书受托“指正”时“痴气大发”,将诗稿改得“七零八落”。胡乔木为难之际,经人斡旋方恢复原貌。这场风波背后,是两位文人对格律的执着:钱钟书求古典精严,胡乔木则重时代新声。而胡乔木力邀钱钟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时笑言“人也能荣官”,更见其对文人诗才的敬重。
在格律与时代之间 胡乔木的诗学理念,始终在“创造新格律体”的探索中前行。他主张新诗应“从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其《挑野菜》的复沓节奏便源自童谣;又提出“每行四音顿”的规范,为自由诗注入韵律骨骼。 他的旧体词更显“旧瓶新酒”的功力。写国庆见闻用“乐土人间信有”,咏雷锋则言“有限成无限”,以白话淬炼古典语汇。正如他晚年自述:“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政治家的胸襟与诗人的赤诚,终在此句达成生命最后的合一。
细读胡乔木的诗稿,仿佛触摸到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文化巨臂的精神年谱——扬州少年的春木秋虫、延安战地的月光歌声、十年风雨中的“愁断魂”、改革开放后的“百花齐吐”。他的诗情从未囿于政治身份,而是以文学之光,照亮了一个革命者灵魂深处的幽微之境。恰似他笔下的高山松柏:“岁寒常忆肝胆在,有限身成无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