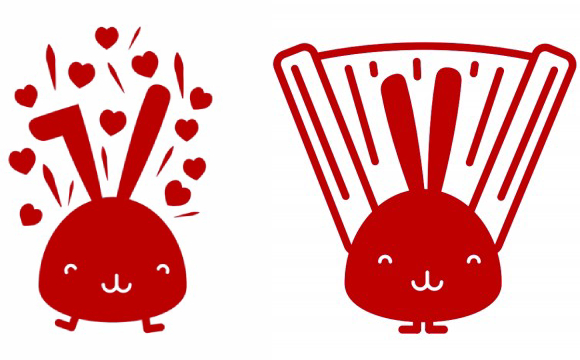|
南宋继续北宋国策,并且与阿拉伯人进行航海贸易,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出口丝瓷茶甚至绘画,南宋货币成为通币,金币甚至成为很多国家的收藏品。南宋的富庶主要来自航海,一派近代化开端的气象格局。 杭州的繁华,要靠海运。那时,浙东沿海一线,是南宋财富的生命线,这一线的港口,也就成了南宋政治存活的命门了,一个是明州宁波,另一在温州。 宋高宗南逃避难温州时,曾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何如取之于外商?一逃回临安,便号召对外开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国策,更以拓海为战略,又发展出泉州港口。 从那时起,宋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并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制海权。其所造海船,经由闽、粤下西洋,过七洲洋,出马六甲海峡,而至印度、波斯、非洲;走东洋,则前往高丽、日本。 高宗下海时,已将亡国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可现在,他懂了王安石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了,原来要靠贸易顺差。当年,司马光指出“天地所生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这还是自然小农经济眼光。 用自然经济眼光来看,财富“止有此数”,是个常量,欲“致国用之饶”,必多取于民,“民不加赋”是不可能的,因此,国与民是对立的。而王安石的说法,则用了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财富是个变量,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经济总量就会增长,以总量增长来“致国用之饶”,自然就“民不加赋”了。通过经济增长,使国与民一体化,形成“国民经济”。 而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形成中,要起推动和主导作用,将个体化的经济行为,导入国民经济增长的统一轨道中,这样的经济增长,就不是国与民之间对立性的此消彼长,而是既繁荣民生又增加国用的国与民的共同增长。王安石变法,当然有缺点,但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而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以此向未来的重商主义,投下了一瞥。 高宗认准了经济总的增长要靠贸易顺差,但他还是没能生出重商主义的念头,而是以消费主义的高级姿态倘徉在艺术栽植的精神花园里——他决定干脆定都临安,将航海贸易顺差都拿来就是。不出几年,杭州已是如下情形:“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得太好了!“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富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美呀!“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乐呀! 在钱塘定都了。钱塘多好啊!放眼望去,“海上明月共潮生”,抚摸当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在这里望海吧,望着海货来!所有海货,都要“抽分”——十分之一进口税,然后“抽解”国库,那真是“无边抽分纷纷下,不尽海货滚滚来”!市舶司,那是皇家的收银台,收来银子,凡我皇家看好的东西,都由皇家限价购买,不用动国库,要靠国家信用,这叫“博买”,也叫理财。下海,就要造船;造船,就要运输;运输,要有货物;而货物,要靠生产,这样就形成了产业链。 不久,经济就恢复了,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已全面超越北宋了。显然,这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人口和土地减少了,可经济总量还在增长,这要靠市场。不断扩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都是大航海带来的。那时,东南沿海人纷纷出海,作为“住蕃”的华侨,开启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他们走东洋,下西洋,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他们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 如同美元,宋币随大航海通行天下,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达,无疑是宋代得以艺术姿态的基础,换来了国家的艺术行为。这便是航海带来的文艺和强盛的立体景象。有了钱,高宗继续访搜北宋流落民间的古董珍宝艺术品,以及重新集结北宋各路画家,继续北宋的文治国策。国家有钱了,可以为艺术而工作,加上与金谈判换取了和平,不用打仗,不用养兵,那就多养艺术家吧。宋代三百多年的王室留下了一个热爱艺术并以收藏艺术为义务的传统,宋代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到了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为艺术而工作的时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不仅参与经济,还参与到艺术工作中来,并以一国之力,赞助和参与创造人类的精神财富。 那些在历史上能够留下光彩一笔的国家,都是有幸能够进入人类精神史的国家,也是无比荣幸的国家。宋代的汴京和杭州,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都有这份进入人类精神史的荣幸。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3)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3)
时间:2015-02-10 11:00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李冬君
南宋继续北宋国策,并且与阿拉伯人进行航海贸易,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出口丝瓷茶甚至绘画,南宋货币成为通币,金币甚至成为很多国家的收藏品。南宋的富庶主要来自航海,一派近代化开端的气象格局。 杭州的繁华,要靠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