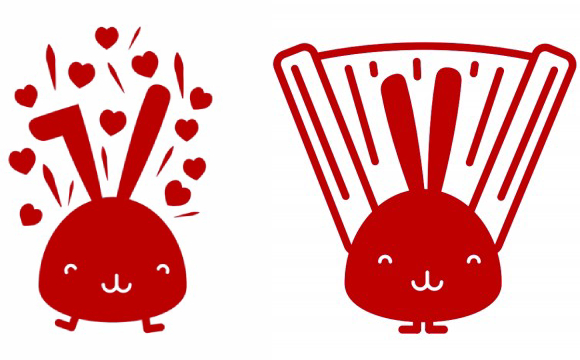2014年,海外汉学家、著名学者黄宗智的《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套三卷本著作中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本报特邀青年学者刘仲敬撰文评述。 站不住脚的推测 作者的史料处理仍然是有问题的。清代诉讼记录的租佃关系和上世纪30年代的跨国经济之间跳跃太大,作者设想的连续性绝不是理所当然的。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是一部名不副实的书,而且名不副实的程度和方式都非常接近于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中国大历史》是干饭加水产生的一锅稀饭。《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构成核心干饭部分,用明代资料形成明代范式,然后将范式推向作者并不了解的其他时期。从《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内容看,此书的正确命名应该是:以1930年代满铁调查直鲁农村的资料为中心,创造“内卷化”范式,然后用这种范式推测今天中国疆土的某些其他部分,并将推测延伸到明清时期。后面两种推测肯定站不住脚。满铁的调查资料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东各地农村和东蒙垦殖地的社会生态完全不同。南方各地的农村情况极其复杂。仅仅珠江三角洲一地,至少就存在三种不能纳入华北模式的形态。其一,沙田垦殖区的宗族自治体。其二,广府绅商作为身份标志的乡族土地。其三,官地、公地、旗地的承种经济。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时间,准确的记录根本不存在。 如果你想用英国历史学家研究敞田制或庄园法庭的方式研究中国农村,就会发现整部中国经济史都建立在稀薄的想象空气和颤动的流沙数据之上。正整数在中国经济史材料中占据太高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损害记录者的审美偏好。如果徐府拥有良田万顷,戚总兵馈赠白金万两,主要不是因为季审法庭曾经调阅爱德华四世以来的判例,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比较铿锵有力。政治正确的世界史集体著作(许多是联合国或跨国组织编撰的)往往将可信度相差甚远的材料平行编列,仅仅为了不让全世界任何地区缺席。对于绝大多数外行读者,这种做法再糟糕不过了。他们如果没有任何历史知识,不会损失什么;如果形成错误的比例感,损失就非常大。一位诚实的香烟商应该告诉顾客:“吸烟有害健康,如果可能最好别买。”一位诚实的历史丛书编辑也应该告诉读者:“西欧之外,近代以前的历史多半是附会的产物。不够全面的历史知识对你的健全常识有害,比完全不懂历史更危险。”在这方面,普通学究的道德责任感还不如普通商人。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质部分重复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1992)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2000)的内容,明智地排除了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口述材料。周锡瑞在义和团研究中未能做到这一点,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可怕的混乱。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诱导性资料是政治气候不断变化的产物,叙述者通常不了解自己之前已经存在的记录,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同一时间地点的事件归诸不同的角色。后来的辨伪者往往用一种诱导性资料纠正另一种,却不知道自己的依据同样不可信。这样层累造成的综合性研究介于科幻小说和诬告材料之间,给后人制造的麻烦比完全不做研究还要多。作者避免了这方面的错误,但他的史料处理仍然是有问题的。清代诉讼纪录的租佃关系和上世纪30年代的跨国经济之间跳跃太大,作者设想的连续性绝不是理所当然的。 无法验证的“内卷化” 黄宗智的范式选择与其说依靠经济学知识,不如说取决于他潜意识的好恶。他怀着恐怖的感情,描写礼崩乐坏的农村。 “内卷化”范式的魔法术语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概念其实属于马尔萨斯学派,斯密和马克思的门徒都不肯承认。黄宗智的意思是:过多的人口分散在家庭手工业内,妨碍了集约化生产和资本积累。投入的劳动力增加很多,产量的增加却很少。产量和供养人口增加,但人均生活水平不增加、甚至下降。华北农村宗族组织不发达,社会严重原子化。国际化和商品化加重了农民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制造了大规模革命和动荡的社会土壤。这条道路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导向资本主义。夏明方用“生存经济”的术语描绘非常类似的现象,更好地解释了他的结论。小农不是最初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人,追求风险的最低化,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种粮食,为了保证生存;搞商品化副业,为了赚零花钱。后者的利润往往比前者高,却并不能诱使他们完全放弃种植业。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国际市场变幻莫测,任何一次商品滞销都能置纯粹的小生产者于死地。这时,即使负利润的粮食种植业都能发挥保险作用。 问题在于,后来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市场分工的细密化势必产生大型中间商,代替风险厌恶者承担风险。慈鸿飞就认为,二十世纪初叶的华北农村经济正在良性发展。资本市场和长距离贸易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用清代租佃关系去衡量是荒谬的。战争、甚至长期的无规范游击战都没有打断华北-东北-日本贸易圈的分工和深化。日本占领时期,天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人口和工业一直在上行。华北劳动力稳定地移居东北,大批转化为产业工人。如果说资本主义道路注定走不通,似乎不是因为“内卷化”社会的原罪,更有可能是因为政治路线的横向干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和市场规范。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不仅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且经历了立法的高潮,大概不是偶然的。从经济上讲,当时的华北是东北的外围。华北输出原材料和劳动力,东北输出工业品。在这种格局下,东北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而且在发展层次上长期高于关内各地。和平共处的结果很可能不是东北的向心力增强,而是华北的离心力增强。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提前抗战,未必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拖延时间对他并不有利。 在抗战和冷战已经发生,而且已经改变发展路径的情况下,讨论“如果内卷化社会继续走原来的道路,能不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多多少少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域。历史实证主义的材料用作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一向都做不到完备。模拟推演主要依靠拼图式的直觉,先有格局然后才能代入材料。如果格局不同,同样的材料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慈鸿飞的拼图更接近西奥多·舒尔茨的算法,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比较接恰亚诺夫理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模型都是可以验证的,而黄宗智和所有历史学家的范式都无法验证。历史本质上不是科学,范式的力量源于神话因素,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明了。黄宗智的范式选择与其说依靠经济学知识,不如说取决于他潜意识的好恶。他怀着恐怖的感情,描写礼崩乐坏的农村。礼俗曾经是一幅温情脉脉的面纱,用和谐的外表掩饰了贫富分化,在商品经济和外国资本的打击下消失了。祖坟出租了,亲人四分五裂。富人移居城市,穷人留在没落的乡村。人心散了,乡绅不再修桥补路了。这是一幅托马斯·哈代或老加图的画面,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无根群众和浪人涌向城市,遗弃了田园牧歌的有机共同体。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刘仲敬评黄宗智乡村研究:神话动物园的标本剥制师
刘仲敬评黄宗智乡村研究:神话动物园的标本剥制师
时间:2015-02-10 11:04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仲敬
2014年,海外汉学家、著名学者黄宗智的《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上一篇: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
- 下一篇:一百件秦代封泥珍品亮相西安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