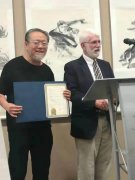|
薛松说:“如果没有那场大火(第二次),很可能我的艺术道路是另外一种样式。大火烧毁了我的很多物品,而这些有形的东西凝聚了我从一个小地方到大上海的全部足迹。大火烧毁了我的欢乐和痛苦,也烧毁了我的郁闷和梦想,这一切都伴随着我昨天的记忆随风而去,剩下的就是焚烧过的痕迹和焦糊的味道。我从这场大火中发现了某种‘痕迹’,找到了一种能让我说话的语言方式……” 这种说话的语言方式便是薛松先从自己某一时期的心境出发,确定说话的对象与主题,如1990年代的政治权力、对话大师、消费文化,2000年以来的都市时尚、传统文化、城市化发展,等等;然后再跑去书店精心挑选一批批与之有关的书刊、报纸,从中剪裁、归类所需图片及文字,并一张张地烧制成“合适”的素材;最后根据画面布局,将这些素材拼贴、制作于画布上,且加以绘画性补笔,创作出了《毛》、《向大师致敬》、《书法》、《古诗新画》、《三毛》,以及都市题材的系列作品。 薛松这种以灰烬和焚烧后的印刷品残片为媒介,通过搜集、剪裁、烧灼、拼贴、补笔等手段将巨量图像和文字残片并置于一个大主旨下的艺术风格源自于对被大火烧尽的个人“昨天记忆”的重新整理,他将那些残存的蛛丝马迹梳理、并置,企图还原自己从砀山到上海的那段历程,进而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其他自己所关注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状态、某一个潮流,通过拼贴搜集到的图像和文字“证据”,用以还原那些逝去的历史及公共记忆。 有时,这种还原也伴随着薛松自身的困惑与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薛松的挪用、拼贴与主旨所处的语境不同,如《舵手》作品里毛泽东的主体形象与拼贴其间,象征着传统文化的书法、古籍残片;《欢迎梦露》形象里密布的中国劳动人民照片;《他是谁?》雷锋背景下的都市明星,等等。当这些内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文本被薛松并置于一个共同的语境下时,画面原有主体的标志性意义则被相对化,这些原材料的含义也因之改变并产生出人意料的“陌生化”效果,从而新的意义从中衍生。对于那些严重对立的内容,也因为此种并置显现出的强烈冲突而具有了批判性意味。 从1995年薛松的此种艺术风格开始明确,时至今日,他已在其开创的图式里探索长达二十年。从这二十年来薛松的作品里,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开放心态并没有让他陷入无休止的范式实验中,就追求前所未有的视觉经验而言,薛松可能更符合传统中国艺术家的心境,即并不将别出心裁视作艺术最为本质、最为高明的要素,而是利用前人的视野,在自己开创的图式内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微妙和完善意义;一方面,他的手法发展自过去,另一方面,其作品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又导向未来;其经典图像和文字的再运用成为我们理解他作品的桥梁,使其作品的含义变得显而易见,让我们无需过多艺术外言语便可会心艺术家的所思与所想。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火痕图像:薛松的记忆拼贴术(2)
火痕图像:薛松的记忆拼贴术(2)
时间:2014-11-24 15:40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陈博
薛松说:如果没有那场大火(第二次),很可能我的艺术道路是另外一种样式。大火烧毁了我的很多物品,而这些有形的东西凝聚了我从一个小地方到大上海的全部足迹。大火烧毁了我的欢乐和痛苦,也烧毁了我的郁闷和梦想,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