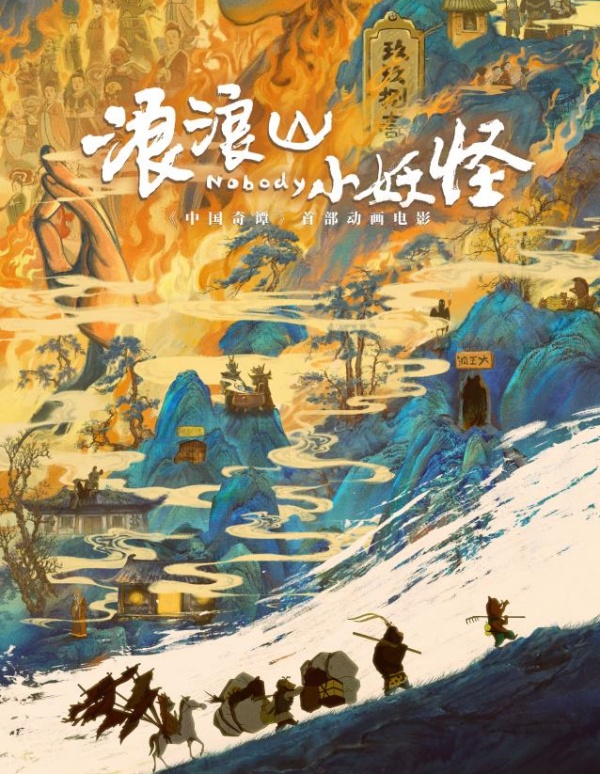|
虽然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提及《红楼梦》极多,传记中说她十四五岁时就写了长篇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但真正作为“红迷”心得的作品是1976年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万字的《红楼梦魇》。1966年张爱玲定居美国,至1995年离世,期间以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此书正是其晚年多年研究的结晶。书中共收入其七篇研究文章,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初详〈红楼梦〉》,《二详〈红楼梦〉》,《三详〈红楼梦〉》,《四详〈红楼梦〉》,《五详〈红楼梦〉》。 张爱玲对《红楼梦》有多熟?她的序中有句话可以佐证,她说:“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看到脂本红楼梦。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红楼梦魇》读下来的感觉很像读书笔记,或者说一个研习《红楼梦》的记录——没有结构章法,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就更没打算给读者舒服地看,但充满了对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的认识。比如她会很注意区分:哪些人物是在作家生命中确实存在的原型?原型走向角色做了多大程度的修改?为什么修改?又有哪些人物是在创作中逐渐自己鲜活起来的?这大概就像一个武林高手面对另一位已经逝去的前辈留下的武林秘笈的揣摩。 林语堂 京华烟云 1951年,胡适请哥伦比亚大学将他的16回珍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做了3套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套送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最后一套就是送给了林语堂。 林语堂和《红楼梦》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从小受的是教会教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16年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时,才开始读《红楼梦》,以补充国学知识。从此,《红楼梦》成了林语堂常读常新的一部书。这位福建人后来在他的《八十自叙》中坦陈,最早看《红楼梦》,也是借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后来,林语堂写的《中国人的家族理想》、《论泥做的男人》、《家庭和婚姻》、《小说》等散文和随笔,都和《红楼梦》有关。 随着对《红楼梦》的情感越来越深,林语堂萌生了将《红楼梦》译为英文的想法,但是担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影响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兴趣和理解,他决定直接用英语创作一部《红楼梦》式的现代小说。于是,便有了《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他自觉借鉴甚至是直接参照《红楼梦》写成的长篇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干脆开始对《红楼梦》直接研究,写出了6万多字的《平心论高鹗》,然后又写了《论晴雯的头发》、《再论晴雯的头发》、《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和《论大闹红楼》等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台湾报刊的特约专栏。 《红楼梦魇》中,张爱玲认为《红楼梦》是一个未完稿,在曹雪芹的十年修改中,有很多人物、情节、结局的变化。“旧时真本”是早期的一百回本,已经完成了的,然而后来曹雪芹继续修订,又加入“风月宝鉴”一书的内容,而这个修订并没有完成。对于今本后四十回,张爱玲相信是高鹗续的,并没有就此论证。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和张爱玲完全不同,他认为曹雪芹已经写完了《红楼梦》,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或者是在原稿残稿上的整理。林语堂这本书中的观点也逐条批驳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林语堂认为如果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只弄出了个八十回,高鹗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续出了四十回,还和前面的情节大体衔接妥当,言语和原著很相近,若是如此,高鹗的才情必远在曹雪芹之上,实在是不合情理的。他的这些观点,引来了众多的质疑与反驳。 1973年11月,林语堂在香港翻译完了《红楼梦》,只是他的英译本《红楼梦》是节译本,全书共66章。与霍克思、杨宪益等翻译家的译本相比,林译本是对原著120回的一种提炼“编译”,林语堂删掉或者精简了原著中很多无关紧要的人物、繁文缛节、性质类似的事件以及大量的诗文。 邓云乡 红楼识小录 邓云乡先生曾经提过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去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人闲聊,俞老先生突然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云乡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 这是一个极小的细节,这部百科全书式小说中俯拾皆是这样的问题。邓云乡研究《红楼梦》的作品,包括《红楼风俗名物谈》、《红楼识小录》等大多是从这些“细微琐事”入手,小到制钱,大到仪礼,不一而足。邓云乡所谓“识小”,出自论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但实际上这些“小者”里面常常会有大学问,涉及经济史、交通史、民俗史、工艺史、园艺史等等。 周汝昌曾经说,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也就是说很多四书八股以外的学问。随着社会剧烈变化,生活习惯,礼仪习俗,动用长物都几乎翻天覆地,二百多年前的人、事、物、相,当时最普通,现在已经难以理解。读懂《红楼梦》,也靠见闻多,阅历多,经过见过多,其实小说家曹雪芹本人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 (编辑:红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