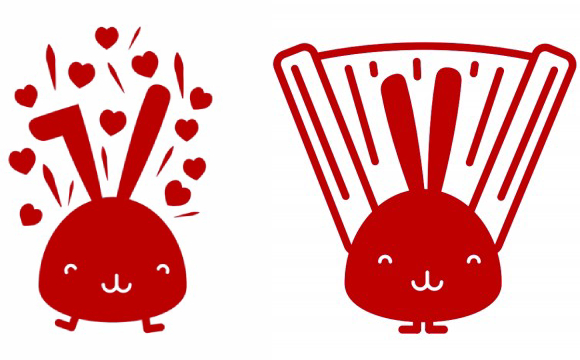|
温普林在文章中写道:艺术家们是亢奋的,他们丝毫没有感受到气氛的压抑。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和理想已经变成现实,现代艺术登堂入室,无上荣光。 七宗罪 第一宗吊丧 来自山西的WR小组成员大同大张、朱雁光、任小颖三人披麻戴孝前来“吊丧”。开幕式一结束,三人便排成一行,大张居中,踏着大展的条幅,非常有仪式感地拾级而上,一进入大厅,大同大张和任小颖先后被组委会人员请出,只有朱雁光一人完成了一楼大厅的行为,范迪安在请他出场时,他高喊一声“我自己会走!”。 朱雁光被请到了办公室中,面对公安人员的质问:“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他脱口而出“大同游击队!” 据说,他们先是在中国美术报看到的关于现代艺术展的通知,明确不允许行为艺术介入。朱雁光在关于吊丧的说明中写到:“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吊丧。” 第二宗大生意 镜头回到一楼展厅,一个角落里,来自浙江的艺术家吴山专立起了一块告示牌:“好消息:为了丰富首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从舟山特带来一些出口一级对虾(长度10cm),数量不多,欲购从速。地点:中国美术馆。价格:每斤十元。”他用一张发表了他作品的美术报包裹着对虾对围观的人们连声重复着:“作品,作品,携带作品……” 显然他把中国美术馆这一神圣殿堂看成了自由市场,而且颇有些针对大展组委会“计划性美术”的挑战。当时的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与范迪安赶了过来与吴山专理论,令其立即停止这一极不严肃的无照经营行为,吴山专他高举起双手作缴械投降状离开现场。 第三宗浪子 来自上海的年轻艺术家王浪一身金庸笔下武林高手的打扮,头顶斗笠,长发披肩,身穿画着神秘符号的麻布衣服,脚蹬一双自制的大头芒鞋。他头一天到了北京就通过美术报的人打电话找到温普林,告知说他第二天有个表演。镜头一直跟随他在展厅游走,直至被组委会成员劝离。最后,他在大型海报展板上留下在“上海王浪”几个美术大字。对王浪而言,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无异于武林高手的华山论剑。他的行为生动演绎出现代美术的江湖感,他本能的意识到定要出手不凡,方能崭露头脚。 第四宗洗脚 跟随镜头重返大厅,在红色布帘围挡的小空间内,艺术家李山一身红色的舞台戏剧行头,旁若无人地洗起脚来,红色的大洗脚盆中画有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肖像,大红嘴唇儿和夸张的笔法,难怪后来的艺术界要将他尊为“艳俗艺术”的鼻祖了。 李山后来回忆他洗脚的初衷:“就是因为心里不舒服,所以想烫个脚,舒服舒服。其实好多行为艺术是针对这个展览本身的,你比如说,有的人搞个”大生意“,是个行为艺术,在卖东西,其实他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就是搞现代美术的这些操纵者、画家、理论家等等有好多问题,比如说规定上海应该画小市民,西南地区应该画乡土色彩的东西,北京就应该搞有政治色彩的东西,等等等等。其实呢,一点都不现代,一点都不前卫。” 第五宗等待 美术馆二楼的一个角落,张念正蹲在那里孵蛋,他胸前白色的纸上用毛笔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 拒绝理论,埋头孵蛋的张念,正被组委会成员孔长安和范迪安以他未交参展费为由劝离,据张念回忆,当时高名潞也正准备冲上二楼轰他,刚走到一半,楼下的枪声响了,所以转头冲了回去。 后来,张念谈起他做这个作品的初衷:“那个时候的美术批评还谈不上什么批评,也谈不上理论,而且那些理论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理论。所以拒绝理论,拒绝理论当然是有很多种解释,不仅仅是拒绝美术理论,也可能是拒绝还有其他的理论,还是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的到来。” 第六宗致日神的? 楼下,王德仁的行为已近尾声。组委会的成员侯瀚如正蹲在地上收拾王德仁抛撒的避孕套。一直有巨人狂想的王德仁在大展上依据脑海中的幻想,制造出一个巨大的长达五米多的避孕套。套子上钉了几排最大号的钢钉,上面写着“致日神的?--戏虐者王德仁”。 王德仁回忆当天:“我看他们组委会的人乱七八糟都在地下忙着捡,我说你捡这些没用,我赶快把大避孕套捡起来之后抱起来,然后一边儿喊就一边儿跑,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们是第一批的革命者,那个避孕套上面的那些大铁钉子,那是中国那么多的现代艺术家的那种精神。所以说那时候我从中国美术馆把大避孕套保护起来。” 我趴在那个美术馆的铁栏杆上喘了几口气,然后这个时候一转身,高名潞和唐庆年过来了,“王德仁,赶快写一个检讨书!”我说“我没犯错误啊”,他说“这个展览封了,赶快写一个检讨书!”后来,厦门达达的成员林春回忆当天:“高名潞当时就站在我身旁,他气愤地说:这些上不了台面儿的家伙!” 王德仁的《美术检讨书》(原文): 由于我的作品引起闭馆表示歉意,比比皆是的避孕套是对旧艺术观念的戏虐,我做这个作品是非常严肃的。 大敬不二 王德仁 89年2月6日 王德仁说:前卫艺术就是要反传统,首先要进行突破或者对他进行革命。 第七宗对话 一楼大厅大厅进门的右首边是高氏兄弟与李群(娃克)的装置“充气主义”,他们作品的对面是肖鲁的装置作品“对话”。两间真正的电话亭,中间挂着一部掉下来的电话机,电话亭正面的玻璃上是一男一女两青年低头打电话的背影,这件装置作品是她的毕业创作,发表在当年的“美术”杂志上。 镜头中,肖鲁梳着一条长马尾,身着一袭深棕色长款呢子大衣出现在她的作品前,唐宋站在她左首边,借枪给她的李松松也在不远处。 肖鲁在自传体小说《对话》里写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走到《对话》前,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仅仅是瞬间的凝视。刹那间,我低下了头。周围的一切都停止,空气凝固了……天堂和地域,仇恨与困顿,胸口的窒息,最后一次冲击我的大脑神经,什么都不存在了……顷刻之间,手指扳动枪的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我打了第一枪。有人喊“再来一枪”,“砰!”我打了第二枪。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纪念89大展20周年:中国现代艺术“七宗罪”(2)
纪念89大展20周年:中国现代艺术“七宗罪”(2)
时间:2014-12-30 15:54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作者:臧红花
温普林在文章中写道:艺术家们是亢奋的,他们丝毫没有感受到气氛的压抑。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和理想已经变成现实,现代艺术登堂入室,无上荣光。 七宗罪 第一宗吊丧 来自山西的WR小组成员大同大张、朱雁光、任小颖三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上一篇:王悦之:台湾第一批赴日本学习西洋油画
- 下一篇:名妓到名媛:中西艺术中的那些悲情红颜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