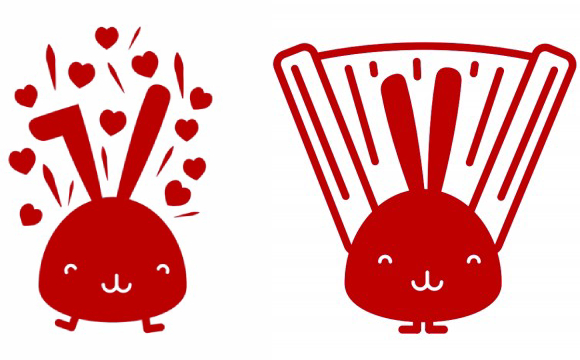|
在东京美术学校为期四年的学习中,王悦之的勤奋精进,异于常人的天赋,让他的老师与绘画同行惊叹再三。他的作品参加过各种的展览,甚至进入过最高规格的“帝展”。一个台湾画家能进入这种展览,对大多日本学生也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故展览一有他的作品挂出,其印象主义风格的自由奔放的笔触,浓烈明亮的色彩,总是引来一片低低的赞美声。 不过绘画只是王悦之的才能之一,他对文学的炽爱与对美术的赤诚是同等的程度。因之一俟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便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深造,同时在北京美术学校任教,没有返回台湾。 王悦之学成之后直接奔向北京而没有回台谋职,与亲人团聚,这个转折看上去多多少少有点突兀。原来在绘画与文学之外,他还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由于台湾早在1895年割让给了日本,因之在这位青年的感受与认识里,他的家国是破败的,寻求救国之道是高于自己的绘画与文学理想的。事实上,早在王悦之读书期间,他就萌动过放弃学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念头,他这么想也这么做了,曾一度离开学校专程到上海想拜见孙中山。孙中山未见到,却认识了接待他的另一个国民党政要、也是孙中山的助手王法勤。这位老同盟会员当初也是去日本留学,后弃学返家闹革命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之间的种种不易与深味,他是体会得很深的人,眼前这位一心想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使他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慨叹之情顿生。他对王悦之坦诚地道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提出由衷的建议,劝他一定要继续完成学业,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形式。 王法勤的坦诚相待与理解,令王悦之倾心感激。而王悦之的俊雅与才华,也令王法勤深感人才难得。也许他们彻夜长谈过,也许他们之间特别投缘,总之在这一次见面之后,王法勤便将王悦之收为了义子,王悦之也正式将原来的刘锦堂的名字,更为了王姓与“悦之”,“悦之”谐自己的名号“月芝”之意,也暗合“我愿意这般”之意。 革命情怀得到理解,个人情感得到接纳,王悦之安然地回到日本,于1921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随后即选择了前往北京,以侨生身份进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文学,并兼职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做了一名学生爱戴的美术教师。在他看来,只有在远离台湾的某处,他的爱国情怀才能落脚,这大概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行为了。他的一生,无论有多少挫败,对自己的国,始终保持了这样一份基本的朴素的情感。 到北京最初的头十年,自觉肩负艺术与革命双重使命的、志大而心高的青年王悦之,仿如获得新生一般。在传统学术思想氛围浓厚、新美术思潮又已春风拂来的北京,他结识了许多学界与美术界的同行朋友,又得到王法勤好友、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照顾。到京次年,他即与留英回国的李毅士、留法回国的吴法鼎等同行创建了研究西画的团体“阿波罗美术研究会”,一起探讨如何融汇西方现代艺术于传统艺术中,又收授学生,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传播出去。 李毅士与吴法鼎都是人中的俊杰,才识渊博又见识广阔,且同样具有爱国的热诚。他们的存在使王悦之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很不一般的踏实感。 这段时期,王悦之在研究古典文学之外,频频参与各种的美术活动,并参加其他重要的美术社团组织。他出任北大造型美术研究会导师,在王法勤的资助下创建私立北京美术学院,接受政府教育部的委派赴日本与台湾专门考察教育,30年代末甚至受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特邀,出任过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西画系教授与日文讲师,再任私立京华美专校长与私立北平美术学院院长。……他是忙碌的,也是意气飞扬的。在他看来,融救国的伟大理想于自己的艺术生涯,将是他平生的最快意事。 在个人的绘画创作上,大约有近七八年的时间,他沉醉于西洋艺术与东方色彩如何融合的新形式中,并迈出过重要的探索之步。事实上,王悦之1930年代之前的作品风格都显现出一种明亮化与情感化的调子,色泽温暖,线条圆润柔美,充溢着一股甜蜜蜜的抒情气息。这既是他源自印象派绘画的非凡功底,也是他的现实生活与心境在画面上的直接反映。 原来王悦之在到北京两年之后,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成年大礼,与一位叫郭淑敏的女子结了婚,婚礼是在义父王法勤的主持下完成的,而新婚妻子的温婉明丽给了王悦之深深的幸福感。这是王悦之一生中少有的浪漫与安宁的日子,他的画面因之充溢着更多的才情与暖调,《镜台》《摇椅》《女像》等,描绘的都是生活的安详感,跃动着他一颗多情的心。 环境与人的变化,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而一个人的容貌,则完全显现出他背后的经历,映出他内心的复杂情感。王悦之走出校门时,是一副俊美的学生模样,衣领雪白硬挺,黑发有精致的中分,俊眉轻扬,眼睛满含笑意。结婚时他已快而立之年了,英气的脸平添了神态上的庄重,却还带有几分的顽皮与忍俊不禁,于此时,他还像生活之外的人。待得再过些年,他似乎才真正走入生活了,戴了眼镜,理了寸头,唇上蓄了短短的胡须,开始着长衫,脸上有了些许的倦意,人的气质渐渐凝重起来。一看就是一位殚精竭虑的先生,一看就知他的内心蓄满了故事和一些说不出来的话。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个自画像中的瘦削美髯公,与其说是他的画笔,不如说是生活把他慢慢变出来的。 在“阿波罗美术研究会”创建的次年,同行知己吴法鼎即于42岁的英年早逝了,再过一年,另一位美术大才陈师曾也在47岁的盛年离开人世,王悦之头次感受到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从更重要的层面上来说,这些同行知己的离去,包括后来他的挚友、文学家刘半农的早逝,使他在精神上遭受了深切的孤单,造成了他生命后期在实质上缺乏支持的局面。 照王悦之对救国与艺术关系的理解,觉得应该是将艺术教育在全国推广开去,将艺术的内部结构充实到更加的完整,将艺术的外延扩展至工艺设计领域。这些伟大的宏图与艺术主张,他不止是在脑中去勾勒,而是以实际的行动去践行。力所不及的,也曾向政府提交万言方案。 不过艺术的推进,文化的自觉,永远是少部分有情怀有才能的人才会顾及的事。何况当时的中国危机深重,关乎国家艺术建设的事,似乎永远只能存在于理想主义的理想中,他注定要遭受挫折与忽视,这不是他个人面对的现实,与他相似的有志青年如上海的陈抱一、杭州的林风眠、北京的徐悲鸿,大都遭遇过类似的痛苦命运。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王悦之:台湾第一批赴日本学习西洋油画(2)
王悦之:台湾第一批赴日本学习西洋油画(2)
时间:2014-12-30 15:52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作者:凡子
在东京美术学校为期四年的学习中,王悦之的勤奋精进,异于常人的天赋,让他的老师与绘画同行惊叹再三。他的作品参加过各种的展览,甚至进入过最高规格的帝展。一个台湾画家能进入这种展览,对大多日本学生也是一件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