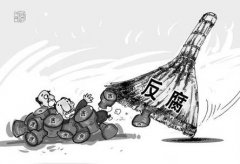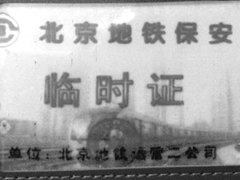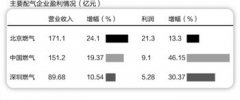当地风俗中,每年的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春节前一天及正月十五,都是祭拜先祖的时刻,也是王家人团聚的时刻。 尤其是清明节,“比春节都热闹”。这一天,王家的男人,几乎都要从各地赶回老家;嫁出去的女人,也大都会回到村中上坟。男人们在坟头互通有无,女人们多坐在坟头哭一阵,和亲人说些家长里短。 这场祭祀活动不仅仅是家庭聚会。在外边成功的王家人,几乎每次祭祖走后,都能带几个族人出去“闯世界”。从新疆回来的一个年轻人说,他就是被在新疆发展不错的族人带走的。现在他一年的收入将近20万元。 “我经常对儿子说,你看看别人家,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回来的时候开着小汽车。你好好学习,也能走出去,光宗耀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汉子说,“人都有一个攀比心理。清明节那天,是对儿子最好的教育。” 老王分析道,祖坟就像个标志,会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家与家比较、孩子和孩子比较,结果形成一股“向上的力量”。 据统计,自恢复高考以来,村里共出了近40名大学生。这个数字,相当于王家周边3个自然村的大学生人数的总和。而那3个自然村的总人数,是王家人数的3倍之多。 “要是没有祖坟,这个家族不会这么有力量。”老王很是骄傲。 一些王家人,还看到了祖坟一种“超验”的力量。 据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当地发大水,整个村子被淹,王家祖坟毫发无损。从此以后,祖坟对于王家人有了“灵验”。即使在平时,王家祖坟上偶尔也会有族人前去祭拜许愿。遇到儿子考大学、老人身体不好等事,都会打发家人到先祖的墓前祭拜。 “儿子读书时,我就常常去祖坟求保佑。结果我儿子就考上大学了。”王家一个中年人说。 老人们则希望“落叶归根”。兵荒马乱的年代,王家有人到外地逃荒,最后客死他乡。族人四处打听。当得知某人尸骨的下落时,就委派他的直系亲属接遗骨回家。目前,这片坟墓中,只有两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墓地位置就一直空着。 “我们家的人都在一起,谁也不能成为孤魂野鬼。”王家一名“应”字辈老人说。有一族人的遗骨,就是他去接回祖坟的。 老王一再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也频频出入祖坟。哪座坟稍有点塌了,他就填点土;哪棵树的枝丫长得碍事,他就会剪掉;阴街上的杂草多了,他就会除掉。 “祖坟是王家的象征,每个王家人的根都在这里。我有义务看好它。”老王说。 我们不反对平坟,但祖先得有个安息的地方 暮色已来临,不远处的村庄开始燃放烟花。一盏盏红色的孔明灯飘起,与点点繁星,共同点缀着欢庆的元宵节。 王家祖坟一些坟包前的红烛一直点着。偶有微风吹来,烛光随风摇曳,忽明忽暗。虽然是墓地,可孩子们一点不在意。他们嬉戏着,偶尔捡到一两个未爆的爆竹,就趁大人不注意,点燃扔在大人脚下,吓得大人跳起来。 有人提议,共同给祖先磕头。于是,几十人就站在王文周墓前,摘掉帽子,为先祖磕了4个头。 过完这个节日,很多在外工作的王家人就要启程,奔赴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虽然王家祖坟圆起来了,但是临近县再次“平坟”的消息,又让他们不安。 “要是祖坟保不住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淡化?”王家一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说,“长此以往,王家互相帮助、互相激励的局面也许就不存在了。” “祖坟关系到家族的发展,王家人都不能袖手旁观。”一个在外地工作的王家人插话说。 本来,这个拒绝透露姓名的男子并不打算回家过年,父母跟着他一起生活。自“平坟复耕”工作开始后,他就一直打探祖坟的消息。当听说祖坟被自己人平掉后,他有些沉不住气,经常在网络上“发牢骚”。 他听说,邻村有人年前去世,这家人不敢请乐队,也不敢请客,“哭都不敢哭”,只能在晚上偷偷将亲人的遗体葬在自己的责任田中,也没有做明显标志。“这是什么事儿?”他气愤地说。 春节放假第一天,他就携妻带子回到老家,收拾出久已不住的老屋住下。虽然艰苦,但他认为“值”。 其实王家人早有行动。去年老王等人平祖坟的时候,他们刻意将先祖的墓碑挖出来,重新竖起。说这是文物,几经交涉,保住了王文周的墓。 那是一块立于清道光18年(1838年)的墓碑,“文革”时为避免破坏,王家人将其埋在地下。 平坟后不久,老王等几个村里的“元老”就商量,每一家至少出100元钱,重写家谱,并在先祖的坟前立两块新碑。这两块墓碑,将刻上王家所有男人的名字。目前,王家人已经筹集近两万元钱。 周口的“平坟复耕”工作开始后,至少在陶母营村,目前还没有建公墓。“我们不反对平坟,得给祖先一个安息的地方吧!”老王说。 王家人就想到建祠堂,把先祖的牌位请到祠堂供奉。这样,即使坟不在了,先祖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村干部,但至今还没有答复。 “先这样吧,大不过再平掉,等清明节再圆坟。”老王笑着对大家说,“王家的魂不会散。”郭建光 (编辑:红云) |
当前位置:首页 >> 调查 >>河南周口村民:不反对平坟但得给祖先安息之地(2)
河南周口村民:不反对平坟但得给祖先安息之地(2)
时间:2013-02-27 09:16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太元
当地风俗中,每年的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春节前一天及正月十五,都是祭拜先祖的时刻,也是王家人团聚的时刻。 尤其是清明节,比春节都热闹。这一天,王家的男人,几乎都要从各地赶回老家;嫁出去的女人,也大都会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