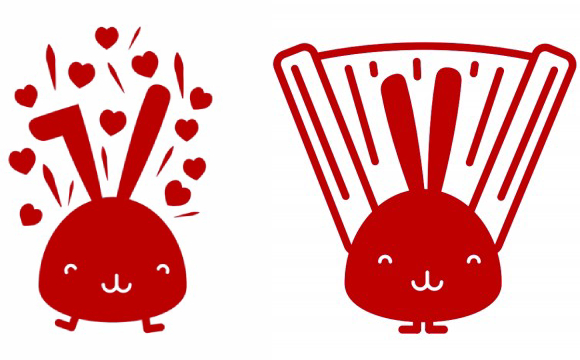|
勉为其难的解释体系 本书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 在马克思的世界中,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资本主义首先完成了欧洲的革命,然后通过殖民主义将革命送到印度和东方,破坏了全世界的传统社会。“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英国殖民者是印度的唯一革命力量,因为印度的村社共同体无法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以此类推,国际资本在华北应该也是这样。 列宁改变了马克思的世界。资本主义由于国际化而增加了力量,已经不再畏惧欧洲的正面攻击。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迂回路线,在资本主义的外围攻击资本主义。因此,殖民主义不再是革命和进步的力量。马克思很高兴英国人征服印度,美国人兼并得克萨斯。列宁却要资助中国国民党和印尼穆斯林联盟,打击远东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日本人在华北扮演了英国人在印度的角色,日本占据的东北扮演了经济起飞的火车头角色。按照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如果农民怀念农业村社表面上的和谐,跟不上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就是历史的淘汰对象。他应该先上火车,变成资本家和工人,然后展开下一轮游戏。如果农业村社产生不了自己的资本家,就让殖民者来做这份工。按照列宁的观点,欧洲的先锋队不能听任历史自然发展。他们要插入外围世界的传统社会,打断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否则后者就会增加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核心区的无产阶级永远丧失希望。这种理论翻译成常人的语言,就是说:中国历史无论原来有没有自发演进的可能,现在都不能听任其自发演进。北伐以后,苏联的远东战略就是这样制定的。华北农村是否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对他们并不重要。苏联设计的历史要替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轨道,就像非洲猿人的后代替代北京猿人的后代。 斯大林经过北伐、抗战和冷战三部曲,完全实现了列宁的庙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研究变得多余和可笑。黄宗智研究的最后部分就属于这种类型。他实际上是在讨论:如果非洲猿人没有进入亚洲,北京猿人有没有可能产生现在的我们?我们现在占据了北京猿人的生态位,能不能以北京猿人为鉴,假装我们是北京猿人的后代?这种讨论出自某种公正感的期许,但只能依靠智力上的不诚实维持。他的意思是:如果某种模式有内在的优点,就不应该遭到外力的替代。如果替代已经发生,无法依靠口舌改变;那就只能修改解释体系,说某种模式本来就令人厌恶,因此本来就没有成功希望,因此历史仍然是合理的、公正的,尤其是可以解释的。一个合格的演化论者不可能接受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演化论的规则都是局部的,时间线是不可逆的。行为主体的命运取决于其所在的生态场域和历史节点,不能孤立地看待。如果“内卷化”社会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注定会导致农民的无产化;那么无产化导致的历史路径仍然不是确定的,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决断。一个越南化的印尼和经过军事政变的印尼大概不会有同样的命运,经过抗战的华北和没有经过抗战的华北同样如此。印尼农村和华北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其说是塑造路径的因素,不如说是路径所塑造的结果。 具体地说:《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30年代的东北经济之所以变成我们所知的状况,主要原因仍然不是内部的社会演化,而是北伐以后的政治决断。如果你讨论地球的能量循环,却不让读者知道太阳的存在,恐怕不是好办法。如果读者因此相信地球的能量主要来自内部,那还不如不读为妙。 以剪贴式组合制造连贯性的幻觉 本书将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华北视为连续演化的整体,跳跃性过大,超出了他的资料所能支持的限度。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话,但神话并不是没有好坏之分。好的神话能够把握脉络,建立正确的相关性,尽管不能保证细节和结论的正确性——这是任何著作都无法保证的。坏的神话却会拆散相关因素,制造错位的组合。本书将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华北视为连续演化的整体,跳跃性过大,超出了他的资料所能支持的限度。人口和土地的统计表绵延五百年之久,即使对于英格兰东南部各郡都太过分了,在华北就不会比哥伦布以前的美洲可靠多少。明初、明末和清朝中叶的华北,即使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延续性都无法保证,主要经济作物则肯定没有连续性。明代的棉花产业和清代的庄园制度如果有什么价值,就是暴露了这些资料多么混乱和可疑。清初的经营性农业当真在扩张吗?确定不是乱后人口恢复和圈地分配体制的文学修辞吗?清朝法律需要为农业租赁而调整?确定不是人口增长—土地细碎化的自然反映?谁真正了解十八世纪的土地分配?即使在田文境整理过后的山东?租佃关系真是在变迁吗?大概是现存的零星纪录可以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吧。地理因素的影响如何评估?尤其是涉及海运取代大运河的时代?这些叙述都是好故事,或是不好的故事。然而,满铁纪录的东北和华北是历史。这样的剪贴式组合不能令人佩服,毋宁说本身就是为了制造连贯性的幻觉,非常像动物园的标本剥制法,用一点点皮毛和几颗牙齿加上大量的塑料。如果拆散成几篇独立的论文,对读者或许会好得多。 明清到现在的农业经济如果有什么可以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没有连贯的系统内发展过程,一再遭到系统外因素的打断和替代。一只母鸡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下蛋孵蛋,她留下的纪录一定是断断续续和令人沮丧的。中国近代史就是这只母鸡,所以你有时很难抗拒诱惑,将现在硕果仅存的这颗鸡蛋说成是最初生下的鸡蛋,有助于尽量忘记已经粉身碎骨的许多鸡蛋,尤其要忘记最后这颗鸡蛋还在十字路口。显然,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刘仲敬评黄宗智乡村研究:神话动物园的标本剥制师(2)
刘仲敬评黄宗智乡村研究:神话动物园的标本剥制师(2)
时间:2015-02-10 11:04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仲敬
勉为其难的解释体系 本书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 在马克思的世界中,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资本主义首先完成了欧洲的革命,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上一篇: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
- 下一篇:一百件秦代封泥珍品亮相西安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