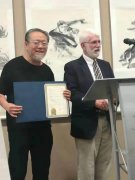读《黟县百工》前,我去过一次黟县碧阳镇关麓村。比起略显商业化的宏村与西递村,关麓显得朴素宁静,村子里人很少,老宅子的白墙青瓦经历了漫长时间,颜色变得不那么纯粹,白墙有雨水浸渍的痕迹,青瓦则褪了色,黑色透出灰来。建筑的线和面还是那样简净,虽然有些宅子荒芜了,院子里长着茂盛的杂草。我们沿着一条小巷子往里走,看到一户人家的门楣挂着块“夹心香干”的牌子,就走进去看看。 这不是个商店,只是普通人家的一间厢房,一张大桌子上备了材料,然后两三个人在做香干,一小沓一小沓地堆放着——另有一些已经塑封好的,可以出售。我买了两包,味道很好。 在读到《黟县百工》“馔饮会”中的夹心香干时,我立刻回想到那趟关麓之行,照片里的大桌子,一叠叠香干,可不是亲眼见过的?于是顿觉亲切。文章写到这小店是夫妻两人开的,“豆干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夫妇俩从结婚做豆干,做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他们似乎没想过当初为什么要做豆干,父辈们干这行,自己也就跟着承袭了父业。他们也乐于守着这份家业,忙碌劳累却也踏实心安。” 这也是皖南乡村让人“心安”的地方吧。农业社会的余晖还未散尽,像是薄暮,却并不只是凋零和凄凉,而依然有一种沉着的美,因为有山川田园,因为有历史人文,然而最根本的,还是有尚未完全消失的劳动着的人,劳作的气息。 一片土地,得有人在这里劳作,才能感觉到它的真实和亲切。在读《黟县百工》时,记忆与记录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是一种乡愁,一种“它还在那里”的欣喜与一种“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自问。这个调查项目由左靖带领安徽大学的学生,历时两年完成,但它不只是一份对濒危工艺的调查和保存,里面有调查者的价值观与感情,并且采用了一种很优美的叙事文体,记录下整个寻访过程:路途、景物、人、场所、物、故事。作为一份调查报告,它调查的不只是百工,而是在寻找百工的坐标点时,呈现出整个的时间、空间与人的坐标系。这份调查报告是合作写成的,但是各部分有一种相当接近的清新而耐心的风格,正如手艺人的劳作,总是需要相当的耐心,成品往往有一种工业制品无法具备的清新之气。《黟县百工》几乎像是画卷一样向读者呈现了乡村生活之美,这种美在百工这里交集,其实却是从时序,从物候,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时序物候里流转的,是人的生死,大部分手艺都是为生活着想的,衣食住行,样样都从自己的一双手里做出来。生活往往俭朴,像刀板香、臭鳜鱼,是年节的美食。平常居家的豆腐干、出门在外的渔亭糕,是生活的底子。但又有艺术之奢与生活之俭相对照——石雕木雕砖雕等等都以工细见长,乡绅阶层将对美的追求的很大一部分附着在了“家”的物质实体上,徽派建筑是乡村文明与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许多手艺也在凋零,但书中写到的几种独特的手艺:做寿衣、做棺材、给棺材上漆——这些手艺却还在顽强地绵延。老人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后之事,里面有一种静默的达观。 在绵延的时日中,乡村之美是在劳作中形成的,它的美在于它的节奏与尺度——节奏应和着自然,而尺度来自于人自身。在经历了工业社会的刻板节拍,信息社会的瞬息万变之后,人们重新追怀起农业社会的节奏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节奏并不“悠闲”,劳作是艰苦的,经验的长期沉淀也积累了快速有效的方式,一个好的农民与工匠,都是极为勤劳耐心的。但手工劳作有一种整体感:它从自然的时间结构中得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来产生一个完整成果,像一个乐句藏在一个乐章之中,呼应着外在的节奏,又有着内在的节奏。这种节奏的美感更多地体现在劳作的过程中,而各种劳作的交织组成了乡村生活。 与节奏互相关联的是尺度,或者说体量问题。因为原材料与劳动者的天然限制,手工劳作不可能有特别庞大的作品,因为不借助于机械,不能无限复制,也不可能有特别巨量的产品。那些小作坊往往都只有很小的铺面,或者在家里生产,到市场中叫卖。人们的需求基本上是俭朴节制的,手工劳作也是在俭朴节制的前提下,追求生活的、审美的、精神的更精致的可能性。这是前机械复制时代才有的,劳作中有更多的投入,使用时有更多的珍惜。朴素的自我,是手工劳作的尺度的根源与依据。 工业化与现代化几乎改变了人对节奏与尺度的感受与认识,人越来越远离了自然与自我,《黟县百工》让我们重新思考自我与自然、与劳作的关系。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读《黟县百工》:重新思考自我与自然、与劳作的关系
读《黟县百工》:重新思考自我与自然、与劳作的关系
时间:2014-11-25 17:04来源:人民网 作者:苏七七
读《黟县百工》前,我去过一次黟县碧阳镇关麓村。比起略显商业化的宏村与西递村,关麓显得朴素宁静,村子里人很少,老宅子的白墙青瓦经历了漫长时间,颜色变得不那么纯粹,白墙有雨水浸渍的痕迹,青瓦则褪了色,黑色透出灰来。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