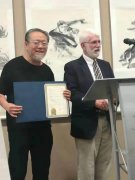文艺不分家,文学和艺术之间本就有座桥梁将二者连接,艺术史上也有很多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很多画家在推出早期作品之前,作品的支持者和认同者并不是美术界的评论家们,相反却常常是文坛里的人。就好比,印象派用跨时代的技法观念去冲击传统美术时,就遭到了官方美术系列的抨击和鄙视,其所认可的是波德莱尔和左拉等一批文人,这些人在诗中和文学中都赞美了印象派的成就,去歌颂印象派画中人物的光彩,说的好像比天上的神明还要美的多。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托尔斯泰与列宾之间关系却极其紧密。 左拉曾经将印象派称作是绘画领域的自然主义,他说,绘画给人的是感觉,而不是思想。印象派画家表现在自然光下的真实,并坚持在自然中写生,这些光的变换使其尽可能多的去捕捉光的瞬间。从整体上而言,他们是将这种自然清新和生动的感觉放在了首位。 我们反观左拉的文学创作,和印象派在消弱其艺术故事性的同时,也将笔锋转向了对平常事物的追寻。虽说在表现方式上多有不同,即印象派绘画转向描绘事物给人的第一感觉和印象,而左拉转向场景的感受性描绘,其在精神内涵上其实是相同的,即对真实感的推崇。二者虽说都是在反映真实生活,但从来不会从题材中引入思想观念,更多的是以包含情感的笔墨来描写感情,传递出个人的生命体验。 波德莱尔与印象派 波德莱尔,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被评价为印象派评论的代言人。波德莱尔与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马奈、塞尚、高更都非常亲密,早期波德莱尔的诗受到欧洲艺坛上最早玩弄“光和影”大师透纳的影响,不过唯独有趣的一点是,后期波特莱尔的诗却又开始影响印象派的这些画家。梵高举枪自杀时,波德莱尔说,“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去。麦田里一片金黄,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 一战之后,毕加索的人物画重又回归传统,例如《读者》,很多人都会认为画中所描述的是毕加索和法国画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以此画来纪念毕加索对故人的深厚友谊。作品中描绘的是两个魁梧的男人并肩坐在石头上,非常自然地将手臂搭在对方的肩膀上,以此来显示出二人的亲密关系。右边会放着书籍,手中还拿着信件,一次去暗示作为文学家的阿波利奈尔。 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被誉为“现代主义之母”。实际上,其和她整个家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胆识,并写出了一段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家族收藏史。20世纪上半叶,但凡是活跃在巴黎的一流艺术家、诗人和作家,都会在斯坦因家的周末沙龙中出现。斯坦因家的周末沙龙也因为野兽派大师马蒂斯、德兰及弗拉曼克的加盟被媒体戏称为“危险狂人的画廊”。 那个时候,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刚刚问世,就遭到了批评家们的抨击和嘲笑,维度斯坦因对这幅冲阿玛尼革命精神的作品一见倾心。在反复犹豫过后,决心购买这幅画。多年以后,他再回忆到这件事情时,说到,“这是一幅光芒四射、充满力量的作品,但也是我所见过的最脏乱的颜料涂抹……如果不是为了用几天时间来消解抵触心理的话,我会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也是从这以后,就开始有无数的艺术家们前往Rue de Fleurus公寓观摩这幅传世之作,其中也包括当时还未成名的毕加索。 列宾第一件见托尔斯泰时,托翁那时候是52岁,画家36岁。列宾用他明察秋毫般的锐利眼神将托老打量了一遍,而后用毫不逊色于画技的文笔写下了一段精彩的记述,将一个有血有肉的托尔斯泰的形象展现出后人面前,就仿佛是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朋友一般。 他是这么写的,“在莫斯科大喇叭胡同我的小画室里,黄昏,一切东西突然都染上了一层晚霞的光彩,在这种特殊的肃穆气氛中颤动着。这时,一位身体强壮、头颅硕大、留着又宽又密的大胡子、穿着黑色长礼服的先生走进来找我。这真是列夫•托尔斯泰吗?原来他是这种模样啊……这是个奇特的人,像一位热情的活动家,虔诚的传教士,他说话时声音深沉而且动人。当他心情激动、情绪很差的时候,声音中有一种悲怆的调子,而在威严的浓眉下,一双严峻的忏悔的眼睛就闪出磷火般的光芒。” (编辑:admin) |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名家 >>那些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
那些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
时间:2014-10-24 16:23来源:新浪网 作者:新浪网
文艺不分家,文学和艺术之间本就有座桥梁将二者连接,艺术史上也有很多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